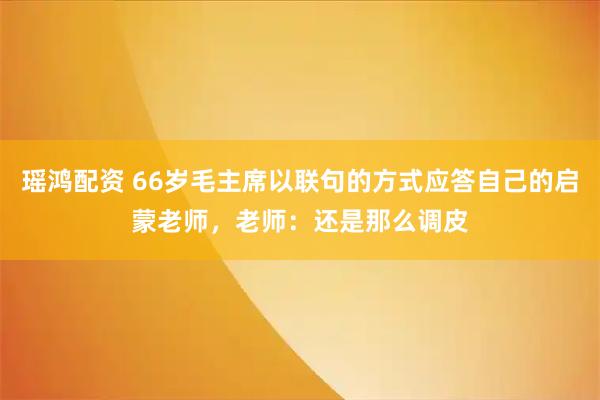
老覃昨天写了一篇文章,题为《1957年,老同学指出毛主席早年被罚的糗事,毛主席惊问:有这事?》。文里讲了一个发生在1959年6月的回乡小插曲:毛主席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韶山,在宾馆设便宴招待乡亲们。他的堂兄兼启蒙老师毛宇居还在,受邀坐在首席。席间,毛主席多次起身向堂兄和乡邻敬酒,毛宇居激动得低声说:“主席敬酒,真是岂敢,岂敢。”毛主席听了笑着以对联的方式回礼瑶鸿配资,意味深长地说:“尊老敬贤,理所应当,应当。”两人相视而笑,周围的乡亲也都笑逐颜开,气氛既亲切又温馨。
回忆起童年读书的情景,老同学们都记得毛润之比很多同学年纪小,但聪明、记忆力好,常常在课堂上“捣蛋”,却也乐于助人,早早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“小头目”。同学郭梓材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毛主席不仅会和老师“作对”,反对旧教条,还带着大家玩兵棋、排队列,发号施令,有板有眼,像个小将军。另一个同学刘洪授也回忆道:老师每次出作文题,润之总是最快完成,还会热心地帮助其他同学修改。
展开剩余55%毛宇居年轻时学问不错,曾出外见过世面,回到静湾一带当起私塾先生。他同样也是毛主席的堂兄,对毛家照顾有加,经常带着毛主席读书教导,生活上关怀备至。但在教学方法上,毛主席并不完全认同堂兄那套保守、死背的私塾风格。毛宇居只让学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其他小说戏曲一律禁绝,这让好奇心强、求知欲旺的毛润之难以忍受。
有一次,毛宇居布置了背诵《孟子》的任务,自己外出访友。教室里,其他学生都规规矩矩地背书,只有毛润之拿着《三国演义》悄悄溜出教室,跑到屋后的一棵大树下,偷偷读了起来。几个时辰后,他带着山间的野果回到教室,分给大家,还特意留了一份给堂兄。堂兄回来后发现他擅自离开,勃然大怒,厉声斥责:“为什么不听我的安排,到处乱跑?”毛润之镇定地回答:“闷在屋里背书头脑发胀,学不进去。我到树下读书,精神清爽,记得牢。你随便考考我就知道了。”
毛宇居要考他,心里还想给他点颜色看看,便说:“那你写首诗赞这井,写不出来就打你的屁股!”毛润之毫不畏惧,挺胸吟诵起一首小诗来,诗中把同学们比作井里的小鱼,表达了对狭隘学习方式的无奈与对更广阔世界的向往。诗里有这样的意象:“天井四四方,周围是高墙。清清见卵石,小鱼囿中央。只喝井里水,永远养不长。”毛宇居听后沉默良久,那天他没有动手打毛润之。从那以后,他悄悄改变了教学方式,课堂上不再一味死记硬背,而是允许更多读物进入学生视野。
这段往事既显露出毛主席少年时的调皮与聪慧,也反映出他早期对传统束缚的反抗与对自由学习的追求。堂兄虽为长者与老师,但在毛润之面前,既有尊重也有碰撞;正是这些早年的交锋与实践,塑造了他后来既有礼敬长辈又敢于创新的性格。
发布于:天津市倍查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